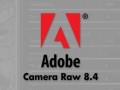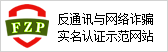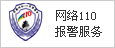我們所處的互聯網,經過了眾包化、社交網絡化發(fā)展,人人參與生產內容,那么曾經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嚴肅媒體該如何適應趨勢?尼克給出了獨特的答案。以下是獨家專訪:
“你看,追根究底,我們都只是講述故事的人。”
尼克·比爾頓(Nick Bilton)在他自己的新書《翻轉世界》(Live In the Future&Here‘s How It Works)里這樣定義自己的身份。尼克是誰?他也是一名科技媒體記者和編輯,他堅持認為,媒體人應該用“講故事”的方式,把科技喧嘩的外在表象及其背后蘊含的深意揭示給普通大眾。在《紐約時報》長達十年的工作經歷,讓他見證了傳統媒體是如何在科技創(chuàng)新的沖擊下忍痛轉型以適應新時代的。
正像“互聯網革命最偉大思考者”克萊。舍基(Clay Shirky)所評價的那樣:“比爾頓不僅生活在未來,也同樣理解過去。” 比爾頓認為,數字技術能應許給媒體(甚至是人類)一個更可想象的未來。這個未來與之前我們所看到的樣子完全不同。
數字化生存,是尼克給每個人未來生活的預想。未來將是一個人人都參與講故事的世界,雖然講述方式有所變化,但嚴肅媒體仍然有存在的價值和重要的意義。只不過要充分利用科技的手段來講一個新的故事:
“社會已經進入權力空白,另一邊會出現什么并不是由公司或者媒體巨擘決定的……消費者在這場討論中也擁有同等的影響力。”
從這段話中,我們得以窺見比爾頓對于科技及其新時代媒體生存之道的觀點。受記者之邀,我從“科技如何影響人類生活及媒體發(fā)展”兩大話題出發(fā),對比爾頓進行了專訪。問答的精華內容如下:
碎片化生活不可怕
記者:你如何看待由技術導致的碎片化生活?
比爾頓:技術是一把雙刃劍。我很享受這種可以獲取不同新聞和信息的生活,但也感覺到自己有時候太過依賴技術,沒有足夠的時間“不在線”。關鍵在于要在工作、生活和技術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有時需要不讓科技產品占據自己那么多的時間。不過現在這對很多人來說都很困難。
記者:能跟我們分享一下你的數字化生存方式嗎?
比爾頓:我家裝了一個Dropcam的攝像頭,如果有人闖入的話,此人的影像就會被記錄下來。這個攝像頭會通過手機振動或提示音的方式給我發(fā)警示信號。我還有一個每天早上稱體重的智能秤,它可以把讀數分享到我的智能手機上,非常方便監(jiān)測體重。我還佩帶腕帶來追蹤自己的睡眠質量,假如今天睡眠不足,明天就多睡一會兒。我的智能手機上還裝了很多App,特別是Moves這款運動應用,它可以追蹤腳步,以確保我的身體每天都可以得到足夠的鍛煉。
記者:谷歌眼鏡和Pepple手表這類智能設備,可以讓我們隨時保持online,也越來越成為我們身體必要組成部分。那么,你認為賽博格(Cyborg)在將來會是一種常態(tài)嗎?或者說是一種不可避免的生活方式嗎?
我認為我們不會成為像電影場景里出現的那種賽博格。但是,我的確認為科技產品將會內置于我們的身體里,比如我我最近在一篇有關石墨烯的文章里寫了這一點。石墨烯是一種新材料技術,可以被用于下一代硬件設備,而且可以直接與人的細胞進行交互。可以想象,佩戴上這樣一款能直接與你身體對話的設備會是什么樣,它還能實時讀取你的健康數據。我們會戴上由谷歌眼鏡演變來的各類設備,還可能有專門圍繞著你自己的WiFi熱點和電力供應,不過所有能嵌入人體內的設備都應該是可移除的。
對于那些想跑得更快或者力氣更大的人來說,他們將使用一種被稱為“外骨骼”的技術。“外骨骼”可以起到外在肌肉的作用,“穿”在身上好像盔甲一樣。請想象一下你穿上這身盔甲一只手就能舉起沙發(fā)的情景吧。這種“外骨骼”技術尤其可以幫助那些身受疾病困擾而坐在輪椅上的人。而對于那些身體需要修復的人來說,“外骨骼”將會成為他們的義肢,這樣的話就更接近賽博格了。
科技要做什么:已經帶來平等和自由
記者:科技發(fā)展速度如此之快,你覺得這是一件令人感到恐懼的事嗎?為什么人們總擔心新技術?
比爾頓:人們擔心新技術是因為,我們作為人類總是害怕變化。如果三十年來你訂閱的報紙都會按時送到你家門口,然后突然間,有人告訴你說必須得在iPad上讀新聞了,那么這種變化就可能造成對既往習慣的破壞,你也會因此而感到困惑。人們會說:“報紙挺好的呀。”當新一代的年輕人開始擁抱變化的時候,年紀較長的人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能接受。
我們總是一開始先對新技術感到害怕,事后才發(fā)現它帶來的好處。不過事實并非全都如此。盡管智能手機讓人們前所未有地彼此聯系在一起,這在之前是無法想象的,然而它也讓我們與身邊朋友變得疏遠了。盡管我們能比以前更快地進行股票交易了,然而那些掌握了更強大技術的股票經紀人卻利用技術本身去進行欺詐。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成千上萬。我想我們需要去擁抱一些新技術,但同時也要明白表象之后還隱藏著更多的東西。
盡管互聯網和移動技術已經很普遍,但像人工智能、神經網絡芯片、機器學習、基因改造等技術對于普通人來說仍然難以在日常生活中接觸到。那么,人們與這類技術之間的距離是不是就會導致恐懼?
知識匱乏的確會導致恐懼。在很多人看來,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聽起來像是一批由兇猛的機器人組成的軍隊要來攻擊我們人類似的。因此,作為一個《紐約時報》的科技新聞報道者,我所做的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要給讀者解釋這些技術到底是什么、怎么發(fā)揮作用以及它們可能帶來的正負兩方面效應。Facebook是一個能夠讓人們彼此聯系溝通的優(yōu)秀工具,但我們使用它的同時要付出隱私作為代價。人們也需要理解其他新技術的這一消極方面。
記者:有這樣一種說法:好的技術可以讓人類獲得自由,但壞的技術卻能夠毀滅人類。你認同這一觀點嗎?
比爾頓:是的。世界上有相當多的領域仍然受制于另外一些人的意見。技術就是信息,而信息就意味著自由。啟蒙時代(Age of Enlightenment)[i]已經讓我們認識到了這一點,而在Google、Facebook和Twitter的時代,我們再一次見證了這一點。
記者:你怎么理解“信息鴻溝”這一現象?
比爾頓:信息鴻溝之所以令人擔憂是因為世界上仍然有30億人口未接入互聯網。這樣一來,一部分人利用互聯網在幾秒之內就能獲得信息,而另一部分人卻仍然生活在數字技術的黑暗時代。我們得找一個兩全齊其的解決辦法,好使世界上的所有人都能相互聯通,而不是像現在這樣兩極分化。
“谷歌氣球”計劃(Project Loon)承諾要幫助發(fā)展中國家的人們使用互聯網,從而擺脫貧困。馬克。扎克伯格發(fā)起的Internet.org也有類似的計劃。不過比爾。蓋茨并不認同用這種方式做慈善。對此你的觀點是什么?
要解決世界上的問題有很多種辦法,對于比爾。蓋茨來說就是治療瘧疾以及其他疾病,而對于拉里。佩奇、謝爾蓋。布林和馬克。扎克伯格來說則是讓人們通過網絡彼此相聯。這兩者之間有一個區(qū)別,那就是蓋茨沒有從治療疾病中獲取經濟利益,而谷歌和Facebook則將極大地從它們所提供的服務中獲利。盡管如此,與其他意圖相結合的利他主義仍然是利他主義。
記者:你認為正在發(fā)生的這些新技術可以最終為全世界帶來平等和自由嗎?就像早些年人們對印刷、電話和互聯網等這些技術寄予的希望那樣。
比爾頓:技術已經為世界帶來了平等和自由——假如政府或某個公司正在撒謊的話,技術就會把這些信息在大眾面前公開,幫助人們看到真相,而我們也會因此感激。印刷技術是這種平等和自由的開端,電話技術幫助信息傳播的距離更遠,現在互聯網的作用又在之前的基礎上更大了。當然,人們也會利用同樣的技術傳播錯誤信息,但真相最終會水落石出。
媒體如何自我救贖:講一個好故事
記者:幾乎所有的傳統媒體都面臨著新媒體的威脅。我們知道《紐約時報》已經嘗試在改變自己的處境了。那么,其他傳統媒體可以從《紐約時報》學到些什么經驗呢?
比爾頓:傳統媒體確實在面臨新媒體的飛速發(fā)展的時候幾無招架之力,不過《紐約時報》很快就對自己進行了調整以適應新形勢。我想我自己在這份已經供職超過十年的報紙里學到的教訓就是,傳統媒體必須要停止以實體產品為中心,而是要開始圍繞網頁和移動設備建設內容。《紐約時報》的做法,是制作網絡以及移動優(yōu)先的互動性圖表和內容,此外還在報道中加入了社交媒體元素。
我們考慮這個問題的最好方式,就是問一問:“如果現在我要開辦一個新聞媒體,我會怎么做?”你很可能首先考慮的是網站和移動媒體,印刷式的傳統媒體則在其次。
記者:《紐約時報》做過哪些成功的互動性內容?
比爾頓:《紐約時報》做過一系列名為《雪崩》的報道,就運用了精彩紛呈的多媒體效果呈現方式,并獲得了普利策獎(記者相關雪崩項目的觀點可移步閱讀:《紐約時報嘗試“雪崩”,重新定義新聞生產的傳統媒體逆襲》 以及 《對不起,<紐約時報>的“雪崩”不是救世主》。
《雪崩》是一種沉浸式的雜志式體驗,結合音頻、圖表和長篇特寫等多種手段對雪崩事件本身及其發(fā)生時一些人的行為進行報道。《紐約時報》在圖表和互動形式方面一直做得很出色,新聞報道、攝影和視頻也同樣出色。所以,當你把以上元素全部組合到一起、又一次性同時放上網,讓讀者可在iPad、iPhone和電腦上同時看到,于是這個作品一下子火了。這是一種很棒的講故事的方式!
記者:《紐約時報》在嘗試做“數據新聞”嗎?你怎么看待由數據驅動的新聞報道方式?[ii]
比爾頓:《紐約時報》已經做了一些數據驅動的新聞報道。公司雇用過納特。西爾弗(Nate Silver[iii]),他是538.com政治網站的創(chuàng)始人和運營者,預言范圍涵蓋從體育比賽得分到政治競選的多個領域。后來西爾弗先生離開《紐約時報》并加入了ESPN,《紐約時報》又組建了一個新的數據驅動的報道者小組。記者們運用數據來講述新一類的新聞故事。
我認為數據、圖表和報道的聯結是未來新聞報道勢在必行的一種形式。我認為,隨著未來可用的在線數據越來越多,這種形式的報道也會不斷增長。
記者:與紙媒相比, 新媒體中也分網站優(yōu)先和移動優(yōu)先兩種,媒體人應該如何對這兩種媒體形式進行區(qū)分?
比爾頓:移動優(yōu)先的媒體通常對于突發(fā)性新聞來說很重要,而網站優(yōu)先的媒體則對于突發(fā)性新聞和非突發(fā)性新聞來說都很重要。在我看來,媒體人應該適應各種形式優(yōu)先的報道。如果新聞突然發(fā)生,那么就得通過各種渠道把它發(fā)布出去,無論是移動設備、網站還是社交媒體,當然印刷的報紙也要用上。
記者:《紐約時報》這樣的老牌報紙來說, 受眾結構影響它向數字化轉變嗎?
比爾頓:事實上,受眾的結構并不影響傳統媒體向數字化轉變。《紐約時報》為了應對數字時代調整得很快,一直在努力嘗試改變,同時還保持了報道的真實性以及嚴格的新聞報道標準和倫理道德標準。我們的讀者也會對一些改變進行抱怨,比如,我記得我們停止刊登股市行情的那天,一些老讀者就不高興。但他們很快就發(fā)現,網站上實時顯示股價的方式要比報紙好多了,時間長了就又高興了。
記者:你認為新媒體是一門好生意嗎?如果科技巨擘接管新媒體的話帶來什么改變嗎?比如亞馬遜的貝佐斯收購《華盛頓郵報》。
比爾頓:我認為新媒體是一門非常生要的生意。向人們傳播新聞和信息以及更多未被揭露出來的重要事實是一項基本的人道主義責任,比如企業(yè)謊言、被政治掩蓋的真相、戰(zhàn)爭暴行等。即便新媒體不是一門好生意,也要把它變成一門好生意。
記者:新聞的表現方式和人們的閱讀方式都已經被互聯網改變,信息碎片化到處都存在,為什么長篇報道還能在報紙和雜志上存在?
比爾頓:我仍然喜歡篇幅很長的內容。我讀長篇報道、看長篇著作,也看時長達幾十個小時的電視劇。為什么呢?因為作為人類,我們還是喜歡好故事,也喜歡有深度的講述方式。書籍已經存在千百年了——我們也本可以只通過快速敘述幾個信息點來講故事,但我們沒有這要做,而是開始寫長篇故事。未來也還會是這樣。 網絡和信息碎片化不會改變這一點。
記者:對記者和編輯來說, 怎么樣才能寫出一篇引人入勝的長篇科技報道呢?技巧重要嗎?
比爾頓:我相信好的講故事的方式最后永遠都會成功。在我的新書《孵化Twitter》中,我寫了一個有關創(chuàng)業(yè)公司發(fā)展及其創(chuàng)始人們因權力和控制欲而把彼此互相排擠出董事會的戲劇性故事。這很容易變成一個枯燥乏味的話題,不過我是帶著一種“誰是真兇”的懸疑感來寫這個故事的,并一直讓讀者去猜測接下來將會發(fā)生什么。這是一種很好的講故事的方式,可以讓讀者也參與到講述過程中來。
我想這種故事講述方式對于新聞報道來說也同樣重要,與你正在使用的媒介形式無關。無論是社交媒體上的即時狀態(tài)更新,還是一篇新聞報道,或是一本書,好的講述方式總會勝出。我在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上都應用這個思路。
記者:人們通常認為,科技媒體會更好地適應科技發(fā)展。那么,像Business Insider這樣的科技博客網站和《紐約時報》科技頻道這樣的門戶式的網站,哪一種更有前途?
比爾頓:這兩種網站都會存在。不過我認為總在不斷追求瀏覽量的網站會遇到瓶頸,因為瀏覽量是不會無限增長的。這類媒體會在某個節(jié)點觸碰到其增長的天花板。而一旦觸及,它們的境況就會急轉直下。看起來有些這類網站在嘗試做一種真人秀似的新聞報道,但是這種方式應該會曇花一現,十分短命。
記者:你怎么看待自媒體和UGC(用戶產生內容)?這些模式會持久嗎?
比爾頓:我認為UGC的模式會持續(xù)下去,因為現在有可以分享這些內容的平臺。然而那并不意味著我的媽媽和鄰居都要開始寫新聞報道了。他們的確可以寫一些與自己所從事行業(yè)或所住社區(qū)相關的內容,也可以寫一些人們喜歡讀的有趣的短篇隨筆,但經驗豐富的專業(yè)記者不會消失。
毫無疑問,一百年后《紐約時報》仍將存在,也仍然在做它所擅長的事情:講故事,報道新聞。